日站君曾经给大家介绍过小红书在上海改造的“运动场”,不知道大家还有印象吗?夹缝里造运动场?小红书4名设计博主爆改上海老弄堂,友:看完心里暖暖的!在上海的市中心,看了那么多地方的纪录片好像上海反倒没有留意过。这次终于找来了上海100每集6带着观众领略上海的弄堂、河浜、建筑、新上海人老房子与新地标老题材与新视角时光穿梭,老渔阳里是当年上海法租界的一条石库门弄堂,回到上海陈独秀就居住在老渔阳里2号,这里。希望《上海老弄堂生活纪录片》一文对您能有所帮助!
上海老弄堂生活纪录片完整版
《上海往事》《上海弄堂》(《上海弄堂》这本书是关于上海风光的书,建议去买实体书,里面有很多上海弄堂的摄影插图,文字也不是那种官方化的语言)《正在淡出的弄堂记忆》《回梦上海老弄堂》(貌似是一本小说,并不是那种专业分析,也蛮好看)《正在消失的上海弄堂》《悲伤逆流成河》(这本LZ应该看过,很悲情的小说,发生在学校、、弄堂的青春故事)
上海老弄堂生活纪录片视频
所谓旧上海,是指抗日战争以前的上海。那时上海除闸北和南市之外,都是租界。洋泾浜(爱多亚路,即今延安路)以北是英租界,以南是法租界,虹口一带是日租界。租界上有好几路电车,都是外国人办的。中国人办的只有南市一路,绕城墙走,叫做华商电车。租界上乘电车,要懂得窍门,否则就被弄得莫名其妙。卖票人要揩油,其方法是这样:
譬如你要乘五站路,上车时给卖票人五分钱,他收了钱,暂时不给你票。等到过了两站,才给你一张三分的票,关照你:“第三站上车!”初次乘电车的人就莫名其妙,心想:我明明是第一站上车的,你怎么说我第三站上车?原来他已经揩了两分钱的油。如果你向他论理,他就堂皇地说:“大家是中国人,不要让利权外溢呀!”他用此法揩油,眼睛不绝地望着车窗外,看有无查票人上来。因为一经查出,一分钱要罚一百分。他们称查票人为“赤佬”。赤佬也是中国人,但是忠于洋商的。他查出一卖票人揩油,立刻记录了他帽子上的号码,回厂去扣他的工资。有一乡亲初次到上海,有一天我陪她乘电车,买五分钱票子,只给两分钱的。正好一个赤佬上车,问这乡亲哪里上车的,她直说出来,卖票人向她眨眼睛。她又说:“你在眨眼睛!”赤佬听见了,就抄了卖票人帽上的号码。
那时候上海没有三轮车,只有黄包车。黄包车只能坐一人,由车夫拉着步行,和从前的抬轿相似。黄包车有“大英照会”和“小照会”两种。小照会的只能在中国地界行走,不得进租界。大英照会的则可在全上海自由通行。这种工人实在是最苦的。因为略犯交通规则,就要吃路警殴打。英租界的路警都是印度人,红布包头,人都喊他们“红头阿三”。法租界的都是安南人,头戴笠子。这些都是黄包车夫的对头,常常给黄包车夫吃“外国火腿”和“五枝雪茄烟”,就是踢一脚,一个耳光。外国人喝醉了酒开汽车,横冲直撞,不顾一切。最吃苦的是黄包车夫。因为他负担重,不易趋避,往往被汽车撞倒。我曾亲眼看见过外国人汽车撞杀黄包车夫,从此不敢在租界上坐黄包车。
旧上海社会生活之险恶,是到处闻名的。我没有到过上海之前,就听人说:上海“打呵欠割舌头”。就是说,你张开嘴巴来打个呵欠,舌头就被人割去。这是极言社会上坏人之多,非万分提高警惕不可。我曾经听人说:有一人在马路上走,看见一个三四岁的孩子跌了一交,没人照管,哇哇地哭。此人良心很好,连忙扶他起来,替他揩眼泪,问他家在哪里,想送他回去。忽然一个女人走来,搂住孩子,在他手上一摸,说:“你的金百锁哪里去了!”就拉住那人,咬定是他偷的,定要他赔偿。……是否真有此事,不得而知。总之,人心之险恶可想而知。
扒手是上海的名产。电车中,马路上,到处可以看到“谨防扒手”的标语。住在乡下的人大意惯了,初到上海,往往被扒。我也有一次几乎被扒:我带了两个孩子,在霞飞路阿尔培路口(即今淮海中路陕西南路口)等电车,先向烟纸店兑一块钱,钱包里有一叠钞票露了白。电车到了,我把两个孩子先推上车,自己跟着上去,忽觉一只手伸入了我的衣袋里。我用手臂夹住这只手,那人就被我拖上车子。我连忙向车子里面走,坐了下来,不敢回头去看。电车一到站,此人立刻下车,我偷眼一看,但见其人满脸横肉,迅速地挤入人丛中,不见了。我这种对付办法,是老上海的人教我的:你碰到扒手,但求避免损失,切不可注意看他。否则,他以为你要捉他,定要请你“吃生活”,即跟住你,把你打一顿,或请你吃一刀。
我住在上海多年,只受过这一次虚惊,不曾损失。有一次,和一朋友坐黄包车在南京路上走,忽然弄堂里走出一个人来,把这朋友的铜盆帽抢走。这朋友喊停车捉贼,那贼早已不知去向了。这顶帽子是新买的,值好几块钱呢。又有一次,冬天,一个朋友从乡下出来,寄住在我们学校里。有一天晚上,他看戏回来,身上的皮袍子和丝绵袄都没有了,冻得要死。这叫做“剥猪猡”。那抢帽子叫做“抛顶宫”。
妓女是上海的又一名产。我不曾嫖过妓女,详情全然不知,但听说妓女有“长三”、“幺二”、“野鸡”等类。长三是高等的,野鸡是下等的。她们都集中在四马路一带。门口挂着玻璃灯,上面写着“林黛玉”、“薛宝钗”等字。野鸡则由鸨母伴着,到马路上来拉客。
四马路西藏路一带,傍晚时光,野鸡成群而出,站在马路旁边,物色行人。她们拉住了一个客人,拉进门去,定要他住宿;如果客人不肯住,只要摸出一块钱来送她,她就放你。这叫做“两脚进门,一块出袋”。
我想见识见识,有一天傍晚约了三四个朋友,成群结队,走到西藏路口,但见那些野鸡,油头粉面,奇装异服,向人撒娇卖俏,竟是一群魑魅魍魉,教人害怕。然而竟有那些逐臭之夫,愿意被拉进去度夜。这叫做“打野鸡”。有一次,我在四马路上走,耳边听见轻轻的声音:“阿拉姑娘自家身体,自家房子……”回头一看,是一个男子。我快步逃避,他也不追赶。据说这种男子叫做“王八”,是替妓女服务的,但不知是哪一种妓女。总之,四马路是妓女的世界。洁身自好的人,最好不要去。但到四马路青莲阁去吃茶看妓女,倒是安全的。
她们都有老鸨伴着,走上楼来,看见有女客陪着吃茶的,白她一眼,表示醋意;看见单身男子坐着吃茶,就去奉陪,同他说长道短,目的是拉生意。
上海的游戏场,又是一种乌烟瘴气的地方。当时上海有四个游戏场,大的两个:大世界、新世界;小的两个:花世界、小世界。大世界最为著名。出两角钱买一张门票,就可从正午玩到夜半。一进门就是“哈哈镜”,许多凹凸不平的镜子,照见人的身体,有时长得象丝瓜,有时扁得象螃蟹,有时头脚颠倒,有时左右分裂……没有一人不哈哈大笑。里面花样繁多:有京剧场、越剧场、沪剧场、评弹场……有放电影,变戏法,转大轮盘,坐飞船,摸彩,猜谜,还有各种饮食店,还有屋顶花园。总之,应有尽有。乡下出来的人,把游戏场看作桃源仙境。我曾经进去玩过几次,但是后来不敢再去了。为的是怕热手巾。这里面到处有拴着白围裙的人,手里托着一个大盘子,盘子里盛着许多绞紧的热手巾,逢人送一个,硬要他揩,揩过之后,收他一个铜板。有的人拿了这热手巾,先擤一下鼻涕,然后揩面孔,揩项颈,揩上身,然后挖开裤带来揩腰部,恨不得连屁股也揩到。他尽量地利用了这一个铜板。那人收回揩过的手巾,丢在一只桶里,用热水一冲,再绞起来,盛在盘子里,再去到处分送,换取铜板。
这些热手巾里含有众人的鼻涕、眼污、唾沫和汗水,仿佛复合维生素。我努力避免热手巾,然而不行。因为到处都有,走廊里也有,屋顶花园里也有。不得已时,我就送他一个铜板,快步逃开。这热手巾使我不敢再进游戏场去。我由此联想到西湖上庄子里的茶盘:坐西湖船游玩,船家一定引导你去玩庄子。刘庄、宋庄、高庄、蒋庄、唐庄,里面楼台亭阁,各尽其美。然而你一进庄子,就有人拿茶盘来要你请坐喝茶。茶钱起码两角。如果你坐下来喝,他又端出糕果盘来,请用点心。如果你吃了他一粒花生米,就起码得送他四角。每个庄子如此,游客实在吃不消。如果每处吃茶,这茶钱要比船钱贵得多。于是只得看见茶盘就逃。
然而那人在后面喊:“客人,茶泡好了!”你逃得快,他就在后面骂人。真是大杀风景!所以我们游惯西湖的人,都怕进庄子去。最好是在白堤、苏堤上的长椅子上闲坐,看看湖光山色,或者到平湖秋月等处吃碗茶,倒很太平安乐。

上海老弄堂生活纪录片下载
1862年6月2日,雨后的暑阴中,一艘奇特的西洋式三桅帆船驶入了上海吴淞口,它的前樯插荷兰三色旗,中樯插英吉利米字旗,后樯则插日本太阳旗,这便是日本明治维新前夜,日本幕府打破二百年的锁国体制后,第一次派遣来华的“千岁丸”。船上的51个日本人中,除了具有代表性的人物高杉晋作留下了《游清五录》以外,其它人则有名仓予何人的《官船千岁丸海外日录》、《支那见闻录》;中牟田仓之助的《上海行日记》、《上海滞在中杂录》;松田屋伴吉的《唐国渡海日记》;随团医师尾本公同的从仆峰源藏,又名峰洁的《航海日录》、《清国上海见闻录》等共17篇文字留传了下来,为我们了解那个时代上海的状况提供了不少详细资料。因为“千岁丸”是刚从英国人手里购置的二手货,驾驶的人仍然是英国人,船上还有船长亨利.理查德多松等英国人15名;又因日本当时与清朝尚未建立正式商贸关系,所携货物需以荷兰商品名义方能进入上海,所以还有一名荷兰商人图莫林古。他们停泊的地点是法租界的荷兰领事馆点耶洋行处,入宿附近一家由中国人张叙秀经营的洋式宏记旅馆。按照名仓的记述,宏记以北不远处就是清廷税关建筑:“江南海关”。
此时太平军占领了苏州,正在攻打上海,根据《北华捷报》的统计,当年上海市区人口骤增到了300万,其中250万是难民。而《吴煦档案选编》1862年统计是:一年内死亡的人数竟然不下百万。名仓予何人说道:“出薛家浜,过江边,见有逃难携妻子住于船中者,其舟不知有几千百艘。”江上、租借和上海城里也到处挤满了难民。其结果正如峰洁所说:上海城内“粪芥满路,泥土埋足,臭气穿鼻,其污秽不可言状。”纳富介次郎又说:当地人把死猫烂狗、死马死猪死羊之类以及所有的脏东西都扔入江中,这些都漂浮到岸边。再加上数万条船舶上的屎尿使江水变得更脏。而且“江上还时常漂着人的尸体。当时霍乱流行,难民等得不到治疗,很多人死于饥渴,也许因无法安葬而将其投到江中。此景真是目不忍睹。”而当时的饮用水就是江水,加一些明矾沉淀一下而已,于是他们随行来的仆从硕太郎、传次郎,炊夫兵吉的尸体,就被埋葬在浦东烂泥渡。高杉晋作对此的态度是:“闻同行渡边与八郎从仆昨夜来急病,今朝冥行云。同行者病客甚多,诸子畏缩,有或促归思者。予以为,一步出国死已决矣,然空死无益,唯身自护吾体无他也。”
四方难民的群集,自然带来了米价腾贵,名仓予何人说:“余至米铺,寻常米价大抵铜钱八十文至九十五文,
纪录片上海人的弄堂生活
老弄堂,是上海特有的民居形式。它代表近代上海城市文化的特征,创作了形形色色风情独具的弄堂文化。北京胡同承载着城市的记忆,而上海弄堂则是这座城市根植血脉的记忆。多少个故事,多少个典故,多少个名人,都与这些纵横交错的老弄堂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黄埔区建国东路36弄,是千千万万上海弄堂的其中一条,放到现在并没有什么名气,过往的行人最多也是稍微一瞥,然后转脸走去。但在旧时的上海滩,这条弄堂可是非常出名的,因为在30年代,这条弄堂走出过上海滩许多位重要的帮派人物。
这条弄堂原名为大康里,随着战争的爆发,很多难民便涌入法租界,短时间内在这周围便聚集了成千上万。在弄堂的对面有一家开业于1933年的容金大戏院,是当时上海滩大亨黄金荣的产业。后来这个戏院改成建国电影院,再后来变成超市,现在废弃无人租用。戏院在当时的上海滩就是纸醉金迷,歌舞升平的地方,三教九流,社会上形形色色人物聚集的地方。
随着难民的涌入,这间戏院便改造成难民收容所。当时的难民主要从事拉黄包车,闲来无事便聚集在一起赌博,有赌博就有欠债,有欠债就有要债的,慢慢地就出现一些狠角色。如“薄刀党”杜阿毛、人力车小车霸蒋富英、崔忠德等。弄堂里打架斗殴的事情经常发生,久而久之生活在这里的难民也习以为常。
但在建国后这些帮派自然也就消失了,以至于生活在这条弄堂里的年轻人都不知道这条弄堂还有过那段历史。如今走进弄堂之中,就如同进入迷宫一般,横七竖八的窄小巷子,房门外老旧的洗手台,房顶上交错着的电线,头顶上方挂满了刚刚洗好的衣服、裤子,看过去五颜六色。
窄窄的弄堂里缺少阳光,地面多是潮湿,“72家房客”,处处都被利用起来。这里原汁原味地保留了上海最平民化、本土化的生活状态,在这里,你能找到传统的、黏稠的、极富人情味的上海生活,也能发现被忽视、被遗忘、即将消失的城市记忆。
跟许多城市边缘化的老街一样,她们很快也将被淹没在历史的大潮中,随着黄浦区旧改征收工作的陆续开展,这些老房子也将留在老城厢的记忆里。不久的将来,这里是否会被另一片繁荣的景象所代替,一段过往即将消失,一代人的回忆即将落幕。
八十年代的上海弄堂生活
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也被称为旧上海,也是中国最早的通商口岸之一,也正因如此造就了上海的繁荣与富庶,当时的上海也是民国政府重要经济命脉所以为什么这就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要占领上海的原因之一。
当时的上海也是几个资本主义帝国的租界,各种不同的文化,资本,种族都聚集到这里使这里成为一个大型的国际都市和伦敦,纽约,巴黎这些城市齐名。也因为如此这里也成为了民国经济黄金十年的一个浓缩体现。当时生活在这里的富人可以说过得相当的滋润,不过就算是一个这么繁荣富庶的城市也有它的两面性,生活在底层的人民就不一样了底层社会生活着形形色色的人,上海的青帮,来自全国各地的帮派都在这片特殊的土地上抢饭吃,而普通的人民群众只能靠自己的汗水,泪水艰难的生活着,他们的酸甜苦辣是我们现代人很难想像的。
可以说当时的上海就像是科幻作品里一个贫富悬殊的赛博朋克城市,富人的灯红酒绿似乎和平民百姓没有多大的关系。
不过也只有在当时特殊的国情才造就了当时如此奇特的上海,而如今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也不再是当时的中国,而上海也早已不是那时的上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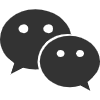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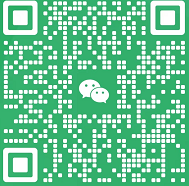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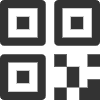

最新问题